- · 中国文学研究版面费是多[01/26]
- · 《中国文学研究》投稿方[01/26]
- · 《中国文学研究》期刊栏[01/26]
读书 | 张新颖:追索48位作家和学者的上海现代文
作者:网站采编关键词:
摘要:(上文摘自《上海文学散步》序,文/张新颖) 责任编辑:朱自奋 作者: 张新颖 你路过虹口区的一所普通学校,澄衷高中,或许会想起它是昔日的澄衷学堂,却未必想得到百多年前,
(上文摘自《上海文学散步》序,文/张新颖)
责任编辑:朱自奋
作者:张新颖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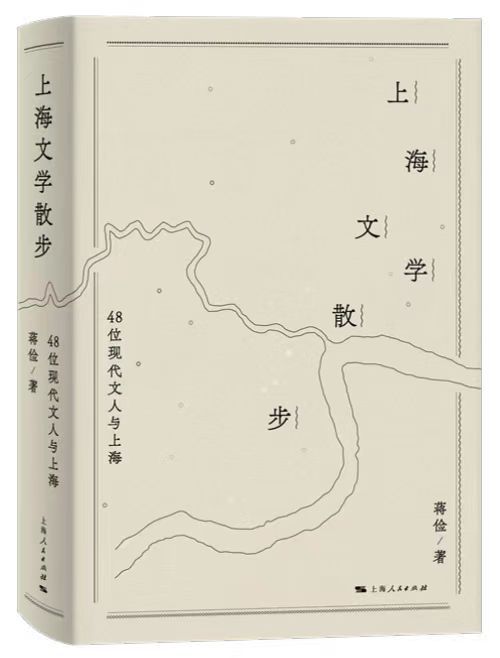
你路过虹口区的一所普通学校,澄衷高中,或许会想起它是昔日的澄衷学堂,却未必想得到百多年前,这里有个学生,给自己改了个名字,叫胡适;你清楚这个名字后来写在了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开端,在他无数伟绩的一生中,有几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,还知道只有小学学历的沈从文第一次站上大学讲台,就是他请来的,但你如果到吴淞,找不到这所学校的一点点遗迹,连一块纪念碑牌也没有;
编辑:金久超
(图源:视觉中国)
这个顽强的作者蒋俭,书成之后,要我写个序。说是因为她最初写了几篇,给我看过,我说有意思;当时如果我说没意思,说不定她就不敢写了。当然,这是夸张,但看着她花了五年时间完成的书稿,我由衷为她高兴,也觉得义不容辞写几句话。说起来,我和蒋俭认识,也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了:那时候她到《文汇报》实习,我算是带她的老师。我这个只有短暂记者经历的人,居然带过实习生,虽然只是名义上的,也够夸张了。
你把它当成一幅旧地图,借助它进入昔日的空间和时间,触摸质感的历史,感受其气息,想象其情境。无疑,它有这样的功用,但这只是一层;
一个现在的写作者,在现在的都市里,靠轨交、公交和脚步划出一条条线,合成的,是现在的地图。它是新划的,却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新地图,它勾连历史上那一个又一个点,标注它们的旧时样貌,也标注它们的现时状况。它是新旧层叠的地图,是历史感和现实感交织的地图。因为层叠和交织而生成的缝隙、深度,你就很难把它当成是平面的,单纯的旧,或单纯的新。
也正因为丰富和复杂,要呈现出来,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它需要案头功夫和脚下功夫的互相结合。做文学研究的专家、学习文学的学生,只做纸上漫游,不迈出文本的大门,不走进嘈杂的街头,不用脚,或许可行;“散步”的作者,却必须用脚,但“散步”之前、之时、之后,也需要材料文献的功课,不做好功课,脚都不知道往哪里迈。
蒋俭著
你知道陈独秀1915年创办《青年杂志》(次年改名《新青年》),但未必知道创刊地在法租界吉益(谊)里;你大概知道陈独秀1932年在上海被捕,但大概不知道他之前两年化名隐居于一条破烂弄堂,叫永兴里;
2022年6月4日
划这样一幅地图,需要努力,需要顽强。它不仅要标注那些存留的、保护的,也要标注那些残破的、拆毁的,不仅标注胜地,也要标注废墟,不仅标注承续,也要标注消失。它要顽强地把文学标注进城市,把过去标注进今天。
你当然知道鲁迅居住的大陆新村,也知道他常去的内山书店,那应该也知道,他到上海,先住的是景云里。要是你还知道得更多,就会想象一些情景:茅盾、叶圣陶、柔石也住景云里;冯雪峰避祸在茅盾家,站在晒台上,可以看到斜对面鲁迅的卧室兼书房,晚上过去聊天谈心,时间长的时候有三四个钟头;鲁迅搬到拉摩斯公寓,冯雪峰一家也随之住进了公寓的地下室;
你读过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,而未曾留心,这是郁达夫住民厚南里时写下的,故事发生的具体地点,是他熟悉的日新里,位于这些年才繁华起来的北外滩;
钱锺书写《围城》时的住所,胡适在上海时期的居所,郁达夫《春风沉醉的晚上》的发生地,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相识地,戴望舒的新婚居所,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的足迹,施蛰存、“新感觉派”与愚园路的渊源,朱自清在福州路杏花楼的婚宴……千姿百态的上海,处处有故事。每个看似不经意的角落、不起眼的建筑,都可能曾有某位作家名人的身影。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你无数次唱过国歌,而没有想到,创作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词时,田汉居住在山海关路;
……
作者在这座城市里穿行,从现在的空间走进历史的空间,走进我们熟悉的、模糊的和陌生的地方:
书稿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之后,学校封控;接着,这座城市封控。我禁足在家60天,每每想起蒋俭的文学散步,她所探访的一处处实地在我脑中乱转而我只能神游,不由得心生感慨;而这个特殊时期的不能散步,说不定能使更多人认识到,在实打实的都市街巷、在层叠和交织的空间和时间里散步,真还未必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小事。
文章来源:《中国文学研究》 网址: http://www.zgwxyjzz.cn/zonghexinwen/2022/0705/1111.html